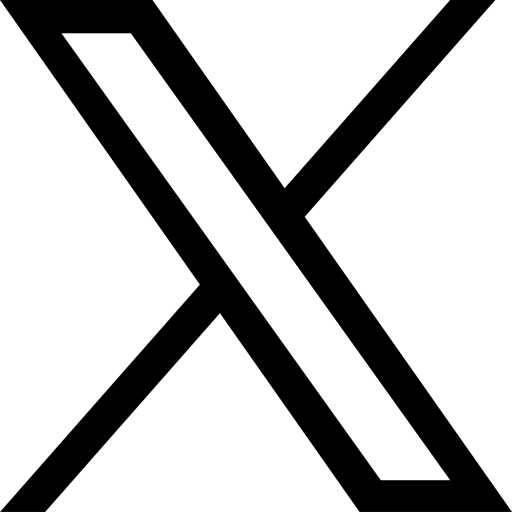26/04/2016
絕色
忘記是1993還是1994年,一個行家邀請我到他的家鄉海南島興隆遊玩,順道在海口市看一批黃花梨傢具。海南島我在1990年去過兩次,頭一次是帶一個開發商跟讀大學時的講師的兄長吳教授去考察地產項目。吳醫生是肺科專家,在廣州教書兼行醫。他不貪污、不受賄,一生清貴,是典型的老一輩共產黨員;他的弟弟吳老師卻一生反共,兩兄弟每次見面都為了共產黨是好是壞這個題目爭論不休,常常令我莞爾。
吳教授有一次跟我說他一生腳踏實地、孜孜不倦地教學,做研究,臨老女兒出嫁,卻連一份稍為體面的嫁妝也買不起,令他有百無一用是書生的感覺。
1990年海南島的基礎建設還是相當落後,從海口通往三亞的高速公路還未動工。我們在海口下機後住進一間三星級酒店,開發商朋友大不高興,嫌酒店太低級、設備太落後,想換一間五星級酒店,但找遍全市也找不到。
每一個人的價值觀都不一樣,吳教授認為住三星級酒店已經很好,我心無所待,隨遇而安,開發商朋友是有錢人,要住好食好,不肯將就,整晚左批評一句,右批評一句,令吳教授和我非常尷尬。
當天晚飯後他們倆上房休息,我走到街上蹓躂,順便找人擦亮一雙皮鞋。我走到一處天橋底,看到一個木鞋箱,便走近坐下,將一隻腳踏在木鞋箱上。天橋底沒有燈光,只靠不遠處的街燈射過去的微弱光線照明。
十分鐘後擦鞋女孩擡起頭,面向微弱的光線,伸出手叫我付錢時,我才看清楚她的面孔。甚麽是絕色?她便是絕色!
如此清秀、輪廓分明、好像不吃人間煙火的面孔,我從來沒有見過。我肆意欣賞她的美貌之時,不由得痴了,良久不能說話。我問她多大,她回答說十七;我問她是不是本地人,她說來自湖北一條農村,是甚麼地方我也聽不清楚。我的普通話從來只有我自己聽得明白,她的普通話夾雜一些口音,我只聽懂大概八成。如此一個絕色少女離鄉別井去海南島以擦鞋為生,實在離我的想像太遠。
我跟她攀談了幾分鐘,直至有另一個客人光顧才起身離開,臨走前我給她幾百元的打賞。她瞧瞧我,又瞧瞧手中的鈔票,一副欲語還休的樣子,我笑笑便轉身走遠,連她的名字也忘記了問。
那次海南島之行可說是一事無成,吳教授帶我們去看的海口地皮,價錢比之前一年貴了兩三倍,開發商朋友當然不買。
兩個月後,吳教授又跟我說「興隆渡假村」有意出售,問我有沒有買家。本來我想叫另外一個開發商跟我一齊去實地視察,但考慮到吳教授不在行、從不知甚麼途徑拿回來的「盤」不一定實在,我決定自己先去看一看環境再作打算。
兩天後的黃昏飛機在海口機場降落,吳教授安排了一個當地低級幹部接機,駕車把我們送到同一間酒店。當晚吳教授的朋友給我們洗塵,邀請我們吃晚飯。
飯後我走到同一處天橋底,看見擦鞋女孩正在忙,便站在一旁等候。她幹完活,擡起頭向客人收錢時瞧見我,便匆匆起身走近我,親熱地叫我一聲「大哥。」我問她吃過飯沒有,她回答說:「還沒有。」我說想請她吃晩飯,她沒口子地答應。
她說想吃家鄉菜,問我吃不吃辣。我答我不吃辣,而且已吃過,吃甚麼都無所謂,隨她喜歡。她將鞋箱交給她的同鄉後,叫我跟她走。途中她問我是否住在酒店房間,可否帶她上房洗一個澡。她說從來沒有住過新式酒店,好想看一看究竟。我唯有帶她上房,讓她見識一番。上到房間,我叫她自便。她的眼神充滿好奇,如劉姥姥第一次入大觀園一樣,左瞧瞧,右瞧瞧,把小小的房間瞧個飽。進了洗手間一會兒,她便走出來問我兩瓶梘液用來做甚麼?我指給她說一瓶是洗髪用的,另一瓶是用來洗身的,她細細聲說:「城市人真講究!」
半小時後,她身上只圍着一條浴巾走出洗手間,一臉天真無邪地在我面前,背著我抹身,抹頭髪,穿回衣服,如出水芙蓉,如天仙的秀麗,讓我想起川端康成筆下的伊豆舞孃阿薰。
吃飯時她跟我說她叫小桐(是不是這個字我不清楚),問我知道她不識字會不會不願跟她做朋友。她說她跟她的同鄉原本想去海南島打工,因為不識字所以找不到工作,惟有以擦鞋為生,希望能賺到一點錢回鄉下做小生意。我見她楚楚可憐、孤苦伶仃,心中不忍,將一千元紙幣塞進她的手裏。
晚飯後我陪她去天橋底拿回她的鞋箱,再送她回家。她的住處離天橋底不遠,拐幾個彎便到。她說她跟幾個同鄉一起住,屋子簡陋,如果我願意,可以坐一會兒,喝一杯茶才回酒店。
離開時她叫我多些去海南島探望她,多多保重身體;我留下一張名片,叫她有困難時打電話給我。
第二天一早吳教授的朋友用一架麵包車把我們送到「興隆渡假村」。到達後我隨處走走,地方很大,但設施落後,隨處都是流鶯,咖啡廳一大堆,中菜廳一大堆,泳池邊亦一大堆,證明渡假村的管理很差。吃晚飯時不知從那裏鑽出一大班人,吳教授逐一介紹,都是地方幹部,我跟他們寒暄幾句便低頭吃飯,沒有心情聽他們的鴻圖大計。
吃完飯喝茶時吳教授跟我說三亞有幾塊酒店用地出讓,問我有沒有興趣看看。其實當年海南島的靚地皮大部份都在當地高官的親屬手上,開發商都不願多付兩三倍的價錢,買一塊前途吉凶未知的地皮。當年又有誰未卜先知,海南島的靚地皮的地價十年八年後大升特升?
第二天吃過早餐,我叫吳教授的朋友直接送我們到機場,訂位乘機返香港。
這一次再去海南島,畢竟跟小桐失去聨絡已有幾年,我因此沒有抱很大的期望可以再見到她。話雖如此,我還是希望可以再見到她,跟她一叙契闊,再瞧瞧她的絕色。
中午在海口下機後我急不及待带行家搭的士去同一間酒店租房,放下行李我便往天橋底跑。我找遍馬路兩邊的天橋底都找她不著,到她的住處找她亦人去樓空。

明末 黃花梨带座無櫃膛圓角櫃一對其中一件 來源:蘇富比
(估價HK$12,000,000-18,000,000)
回到酒店時行家問我匆匆忙忙去找誰,我沒有說。他說已約了黃花梨傢具的貨主,一個小時後他會駛車到酒店門口接我們去他家睇貨。傢具是真黃花梨,但比較殘舊,一對圏椅,一張畫桌,一個櫃和兩張几,開價只是幾十萬人民幣,不貴。我問貨主可否送到香港交收,他不願意,他說可以代我找人拆榫頭,貨到香港後我自己再找人重組散件。他又說我遲些反正要找人維修,這樣安排最好。當年我做木器的經驗淺,不知道那幾件黃花梨傢具其實是寶,最終竟然放棄購買,白白錯過了賺錢的機會。
「買貨定真假是一難,定價位又是一難,兩難既定,剩下的是心痛與後悔的抉擇:花錢儘管心痛,時光慢慢流逝,心痛慢慢淡忘;該買不買的後悔倒是一輩子的牽掛。」許禮平說的真對,那幾件黃花梨傢具,我真的牽掛了一輩子。
明式傢具市場這十年八年已是神州大款的金谷園了,我等尋常書生遊園都怕驚夢,遑論買進賣出!
最終我再也找不着小桐。緣起縁滅,緣聚緣散,一切皆是天意!
《經濟通》所刊的署名及/或不署名文章,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並不代表《經濟通》立場,《經濟通》所扮演的角色是提供一個自由言論平台。
【與拍賣官看藝術】畢加索的市場潛能有多強?亞洲收藏家如何從新角度鑑賞?► 即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