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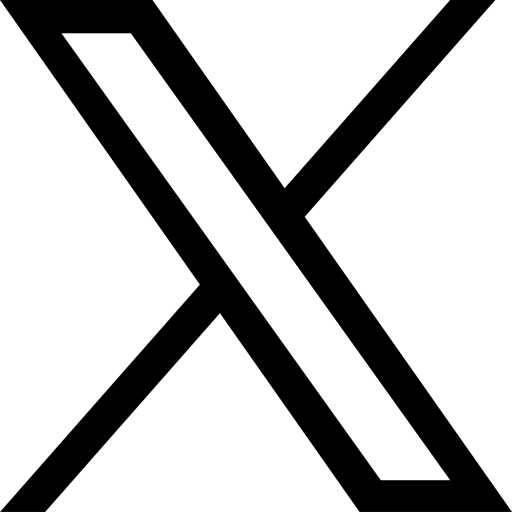
18/12/2024
以散文式代替獵奇式:《爸爸》為精神病患者洗污名,重塑生活的質感
先旨聲明,本文不是影評,是純粹抒發一些觀影感受——《爸爸》裡的父親,跟同期上映的《破·地獄》與《得寵先生》裡的父親不同,驟看平淡,但蘊含social contexts,以及「男人之苦」的克制情緒,儼然成為年末電影某種符號。
翁子光跟婁燁不同,後者說他沒有權利向觀眾過分宣揚個人視角和觀點,影響觀眾做出觀影選擇;前者卻也恰如其分,透過訪問闡釋一些細節原委,幫助觀眾解讀他拍這套「溫情倫理片」的初衷,而其中一樣就是思覺失調。
大眾對思覺失調的含義尚存在很多誤解,只理解為「意外」甚至帶來暴力。現實中是少數,更多是像《爸爸》中正值青春期的兒子厚明,或我以往處理過的輔導個案,某些案主經歷生活上來自學業、工作或個人追求的壓力,如長期累積而未能有效排解,加上腦內神經傳遞物質失衡,便可能誘發思覺失調。厚明性格被動、自覺內心世界沒被聆聽、認為父母只顧24小時工作欠缺溝通,也曲解老師的講課,在長期沒有獲得適切抒發下終釀悲劇,但這不是電影主軸。
飾演厚明的蘇文濤(Dylan)首次擔綱,跟「妹妹」厚恩(熊諾頤飾)一樣,兩位小演員自然從容沒怯場,生活感強,這得歸功翁子光把Acting Coach 這崗位正規化,邀請表演指導Wing Mo的巧置,無意中替香港建立一種電影文化,離開慣常奇案片的獵奇表述,反璞歸真呈現一則社區突發事故,發生前後的生活落差,重新觀看《爸爸》一家人如何生活,透過片段,鋪展出家人關係是否如我們預設的想像。
翁子光駕馭電影語言的功力沉實,利用鏡頭捕捉每個場景。不論是居所、K房、精神病院,還是深夜球場,只讓空間說話。那飄移的光有點像奇洛斯夫斯基的《兩生花》,那些場景,沒有甚麼劇情推進,只是慢慢地說生命的靈動、時光永不回的流逝,三花與機械貓多啦A夢的符號互換,滲著戲味。
當然,絕對不能不提「平民劉先生」劉青雲。他沒有在演永年,他只是借穿上永年的衣服,過永年的生活,感受事件前後帶來各樣無處宣洩的情緒。與其說「天花板」,劉先生只是在表達一種男人的沉澱、某種父愛的直率,一如我去年在京都某酒店法國餐廳偶然碰到他與太太坐在鄰桌,自然從容大快朵頤。有趣的是,或許演繹過永年的真誠,再看青雲近來數個訪問,彷彿也多了一種鬆弛和坦然。
在《爸爸》裡,我們看到對希望、苦難,以及詮釋的虛與實。翁子光對精神病患者不施加批判所表現的人文關懷,相較前作更觸動人心。若說療癒,略嫌過於簡單,尤其對於「釋懷」的透析,何用執著於放下,純粹與遺憾、無奈共存,爸爸依舊生活著,選擇記住了一家人有過的日常快樂,例如笑爸爸貌似戇豆先生,幾千蚊買數碼相機,借阿女的手寫板寫情信⋯⋯於是,劉青雲在戲外也說「唔使成日諗住放下㗎」,故此特別喜愛谷祖琳唱K唱走了調的一個「失」字——此中有深意。
《經濟通》所刊的署名及/或不署名文章,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並不代表《經濟通》立場,《經濟通》所扮演的角色是提供一個自由言論平台。
【etnet獨家優惠】親手炮製母親節&端午節海鮮盛宴!使用優惠碼享95折優惠!► 立即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