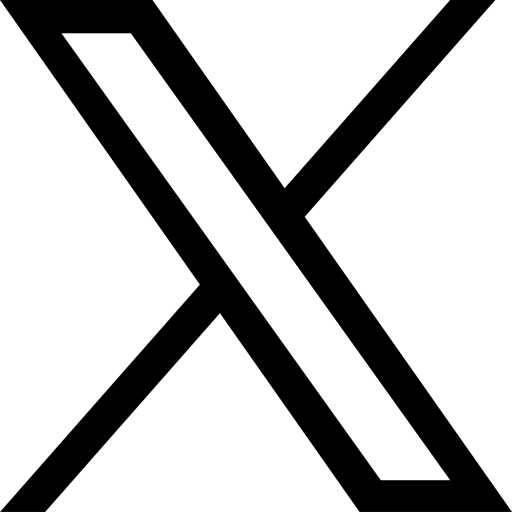09/02/2021Text: Helena HauPhoto: Alex Yeung
Immerse myself in art:「喜歡就是,連做夢都在想!」— 90後女生一場沒有終點的馬拉松
當年輕一輩都覺得中國藝術沉悶時,有這樣一位90後女生:對中國文化和藝術有著不可言喻的著迷,而這裡所指的中國藝術,不僅僅是近現代的水墨發展,而是從宋元明清為始……當中究竟有甚麼吸引著她,讓她不顧一切投身其中?
她,是徐子晴,Karen;一個獨立策展人,一個文獻研究員,一個修讀藝術史的博士生。喜歡藝術,尤其對中國藝術著迷,那是因為爺爺在她兒時埋下的種子。子晴的爺爺畢生從事教育工作,自小和爺爺親近的她,接觸很多文學類書籍。初見她,覺得她斯斯文文,談吐大方;及肩的順滑秀髮與白湛的皮膚,顯得她份外清秀,透著絲絲文人氣質。後續的訪問,每次見她都是素色衣著,黑白灰之間帶著一絲沉靜。
Karen的求學階段,與很多人大同小異;但在升讀大學選科的分岔路上,她沒有按興趣選讀藝術科目,考慮到父母的建議與未來出路,她當時選擇了一條人人公認的康莊大道—到瑞士修讀工商管理。
在踏入藝術圈、從事畫廊工作前,子晴曾有一段時間在管理公司從事行政工作,那是她剛從瑞士畢業,回港後的第一份工作。或許是習慣在瑞士生活的慢板節奏,香港的急速與反差讓她不得不思考自己的路還能怎麼走;特別是每天上下班,看著周邊鱗次櫛比的摩天大樓,走在人來人往的中環天橋上,走慢一點,甚至會聽見身後的人有微言……難道要有所成就,真的要繼續這樣走?難道真如父母所說,藝術作為興趣,只能是興趣?
機緣巧合下,子晴進入了著名畫廊榮寶齋工作,一做便是三年。榮寶齋是康熙11 年的老字號畫廊,於2013年進駐香港,是當時極少數專營中國藝術的畫廊。而中國藝術於子晴而言,有種熟悉感;一方面是爺爺的澆蓋,另一方面亦是從小跟著爸媽出差各地,接觸歷史文化、名勝古蹟所得著。「我覺得書畫的世界很吸引,在裡面有很多歷史的痕跡,我自己也很喜歡中國歷史,而書畫的內容往往跟歷史是緊扣的。」子晴說。
遲來的叛逆
由身處商業機構到藝術畫廊,對子晴來說感覺大不同。「雖然都是中環,但那是一個很寧靜的空間,而且是被藝術品包圍的空間!」伴隨著興奮與期待,子晴踏入從未涉足的藝術行業,誇張點說,也許這就是她人生的一個「叛逆」。回想起剛進入畫廊工作時,她最大的掙扎與困難是很多東西都不懂;從日常的畫廊管理到公關、策展、銷售等,她都需要兼顧;但她自覺十分幸運,入行便遇到了「恩師」—— 王衛。
王衛先生是當時香港榮寶齋的總經理,同為榮寶齋鑒定委員會委員,亦是著名的中國書畫鑒定專家徐邦達先生的入室弟子,從事書畫鑑定及研究工作三十餘年。那時候,子晴每天辦公的位置就在王衛先生旁,總經理的房間內;每日午休時間都有一個「小測」。她的師傅一手叼著煙,一手翻著那本厚重的《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以半躺的狀態,翻到哪考到哪……「頭一年的壓力真的很大,印章作為書畫、鑑定來說是入門,做這一行一定要懂;而那種壓力是,你回答不上,對師傅、對自己都很難交代,所以要花很多額外的時間溫習。」那本書收錄了以隋唐為始,到近現代如齊白石、張大千、吳冠中作為尾聲的印章;印章好比藝術家簽名,可以追尋到藝術家在不同時期及不同風格的繪畫痕跡,甚至生平;現在來說,那本書子晴已是滾瓜爛熟,但還是會經常拿出來看。
在畫廊工作,不少人以為只需打扮得漂漂亮亮、穿雙高跟鞋,笑臉迎人便可;何止於此?「在展覽開幕前,我試過無數個晚上,坐在畫廊的地板上弄畫框、托裱、幫每幅畫作拍照,還要搬搬抬抬……還試過在開展前一刻,鞋子都沒穿,在畫廊裡掃地、撿垃圾;然而下一秒就要開幕了,要馬上換好裙子、穿上高跟鞋、化好妝,笑著迎接來賓。」每每走進畫廊,走進這個被藝術品包圍的空間,總能感受藝術世界的一絲寧靜;然而這背後的反差,就如打仗般急忙、準備到最後一刻,也是現實。「一場展覽由開幕的一瞬間,其實就是最好的呈現;但在開幕前,卻要花費最大的心力和時間,克服很多困難才走到開幕一刻。」
有展覽時,籌備;沒有展覽時,子晴就央求經理讓她走進畫廊的儲存室,看看書畫作品;「研究中國書畫及文化,最核心的東西就是不斷訓練自己的雙眼,然而在畫廊裡,就有無限的空間和條件讓你對著原作學習。」
子晴至今入行大約八年,中間經歷了不同的歷程,要數當中最大的轉折點,就是離開了工作三年的榮寶齋,重投學業。「當我再次策展,或者面對古書畫這個領域時,我覺得我到了一個瓶頸位,就是美術史儲備的知識不夠。」如是者,她投考中央美術學院(簡稱央美),修讀藝術史碩士,那年是2016年。
央美無疑是內地最頂尖的藝術學院,集齊全國各地美院最優秀的學生。當父母聽到子晴想投考央美修讀碩士時,並沒有大力支持,其中一個原因是,到歐洲修讀藝術史碩士只需要一年,在香港也不過兩年,而央美則要三年!但子晴很清晰,她相信若想要繼續深入探索中國美術史的世界,便需要到一個擁有全世界最多、最精書畫作品的地方,那就是北京。「北京有故宮、國家博物館及美術館,我可以看到最好、最頂級的中國書畫收藏。」
對於她中國藝術的喜愛,繼而投入在外人看來沉悶的學術研究,就連香港著名建築師和水墨藝術家馮永基先生都說:「沒有多少個年輕人像她那般傻。」馮永基醉心於水墨創作,很多人認識他是因為他的建築貢獻,當然作為一個建築師,建築是他畢生喜愛;即使退休後,說是全心全意投入水墨創作,其實也放不下建築。子晴認識馮永基是在一次慶功宴上,那時她剛替水墨畫家黃孝逵先生策劃完一個展覽。機緣巧合下,認識了他,子晴更在離開榮寶齋前,幫他完成了《天地凡間》的展覽,那是2016年,也算是在離開畫廊前的一個心願。
修讀完三年碩士課程後,她沒有馬上回港,繼而報讀了央美的博士課程。在央美的香港學生,數數手指,子晴說應該不到五位,而繼續修讀的博士生,只有她一個。回想起初到北京學習,她自覺不習慣,從生活大小事、水土不服,甚至語言,再到自身對美術史認知的薄弱,需要額外花很多的時間惡補和融入當地的大學生活……這一樁樁她都走過了。
央美的學制有如傳統院校的師徒關係,余丁教授是她的碩士及博士導師,亦是中央美術學院藝術管理與教育學院的院長;於她而言,余丁教授就如恩師王衛先生般,給她很大的支持與幫助。余丁教授除了在學術研究上指導外,同時亦給予子晴很多做大型學術研討會項目的機會,讓她可以更純粹更真誠的深造。
「我一直相信你要找到一樣自己喜歡的東西,而我很幸運,可以將自己的興趣和工作,甚或人生目標結合。」繼續碩士論文的中國書畫收藏史研究,子晴近兩年著眼於北美的中國書畫私人及博物館收藏,比如從70到80年代起,私人收藏是如何跟博物館收藏發生關連?北美的博物館為甚麼要建構中國書畫的陳列展廳,又是如何開設重要的展覽,邀請這麼多世界知名學者去討論並關注中國書畫藝術?私人收藏是如何和藝術品市場,比如拍賣行發展?
「這不是單純的個人行為,而是影響着博物館的一個組織結構和體系,當這個體系產生變化的時候,會對地區性有一定的影響。」為了更切身及深入的研究,她每年總有三個月時間走到紐約,去北美的博物館倉庫看畫,甚至拜訪當地的華人藏家,坐幾小時火車,親自去他們家裡看原作……說到這裡,馮老師再次慨嘆、拍著大腿說:「我自己做建築做了這麼多年,也不會為了一座建築飛去看,她真的只為了看一幅畫而飛過去,我覺得我的決心不小,還有人比我有決心!」
亦多得王少方先生的幫助,子晴的碩士論文得以延續並影響至今的博士研究。王家是全球收藏八大山人書畫的藏家,而王少方則是王方宇教導之子,在王方宇過世後,他將大量收藏捐贈給美國Freer美術館,子晴的碩士論文便由他們家族在北美收藏開始研究。
連做夢都去想的事
除了學術上的研究,子晴亦參與很多展覽策劃,如助理策展「Affordable Art Fair 香港癌症基金藝術慈善拍賣」、執行策展中國美術館及天津美術館「黃孝逵水墨藝術展」、「早春黃山行」水墨、攝影聯展;「ink asia水墨藝術博覽會」香港水墨創意會策展人等等……其中,不得不提的是2018年的「黃孝逵水墨藝術展」,那是極少數的香港藝術家能在中國美術館辦的個展。「要進入國家一級的美術館是十分困難的。第一,我們的群體比較小;第二,藝術風格與內地有較大的差距。」而目前在生的,只有黃孝逵先生一位,已故的就是呂壽琨。「作為一個香港人,我有責任去找一些機會,帶香港的藝術或藝術家,去不同地方做交流。」子晴說。
「藝術這件事我經常都會想,有時連做夢也會夢到!我想真正的喜歡,可能就是無時無刻的被喜歡的東西包圍著,而不僅局限於工作和學業才去想。」「喜歡就好」這句話不僅印在她的腦裡,就算是以前在畫廊工作,協助藏家選畫時,她都是說:「喜歡就好」。
你說做藝術苦悶嗎?學術研究孤獨嗎?每天和書畫、文獻打交道,子晴卻覺得難得,難得能堅持。以藝術家為例,他們能在歷史上留名,首先是堅持,願意接受這漫長過程中帶來的孤獨感,而這種孤獨感,子晴形容為「沒有終點的馬拉松」;因為在過程中,你不會知道自己得到甚麼,「但你會感受到對藝術的熱情與忠誠。」
做學術研究或許孤獨,但勝在路上伴隨著喜愛、熱情,同時也有伯樂明燈。無論是恩師王衛和余丁、導師王少方,還是工作與生活上遇到的馮老師與黃老師,他們所帶來的指導和啟發,都讓她覺得這條路並不是那麼孤獨。或許就如她所說,「人生的道路,可以慢慢走,但從不後退,同時要對自己有所期待。」
只要喜歡,就好。
影片轉載自: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 Greater Bay Area Homeland Youth Community Foundation
【你點睇?】【你點睇?】中美經貿會談獲實質進展,雙方發佈聯合聲明並互降關稅。你對接下來的磋商是否有信心?► 立即投票